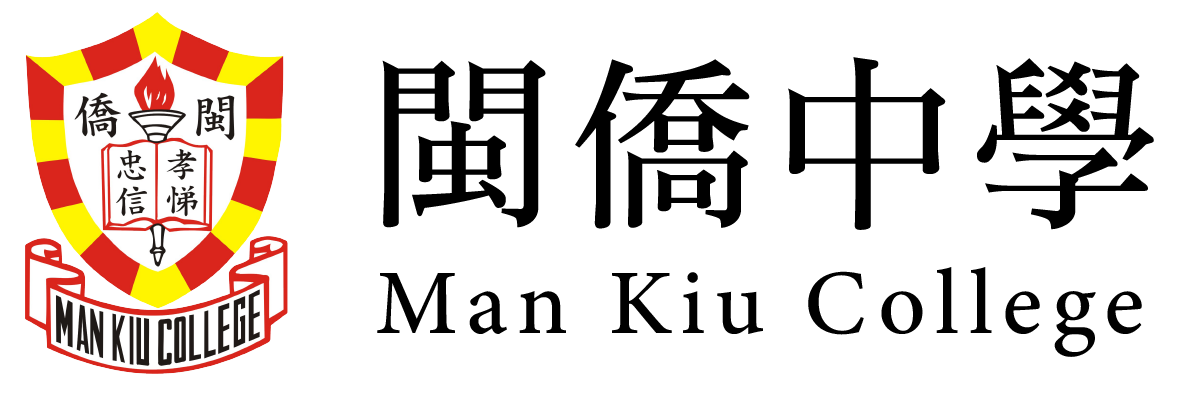2018年11月28日 : 星島日報 | 楊恩華同學 : 無形曲譜手中奏 視障青年憑二胡發光

只得半成視力的楊恩華,自忖若無遇上二胡,或許只是整天自怨自艾的「廢青」。那年十三歲,二胡將恩華從低谷拯救出來,矇矓不清的前路,突然出現方向,別人用五年時間才考到十級二胡,他發了狂去考,兩年就達標。去年恩華視力又下降,大字曲譜都不再管用,但為奔向職業演奏的夢想,還得想盡辦法拉下去,老師讀譜,他背譜,最後花上半年時間記熟歷時二十九分鐘的樂曲。演奏是公平的,持着琴弓,靠住努力,揉出樂韻,誰敢說他沒能力踏上大舞台,以二胡綻放光芒?
今年二十二歲的恩華出生於黑龍江哈爾濱,他因早產導致視網膜受影響,先天只有五成視力,其後更於小六患上白內障,視力再跌至一成,頂多只見到人的輪廓,看不清相貌,「成績由那時開始變差,主流學校老師不懂教我,所以我整天自怨自艾,沒甚麼目標。」這個情況一直維持到他中二轉讀特殊學校,遇上「知音」為止。
老師助抄大字版曲譜
十三歲那年,恩華祖母不忍見他繼續頹喪,有見及二胡跟視障人士頗有淵源,譬如有知名樂曲《二泉映月》、人稱「阿炳」的華彥鈞正是失明樂手,祖母遂決定讓他發展二胡專長。恩華初次拿起二胡,當下第一種感覺是好奇,他發現此樂器若能拉得好,像會說話的人,拉不好卻是「劏雞」似的,他萌生興趣想認識更多,「反正我沒其他事做到,當時人生突然找到方向,有了新興趣作為寄託。」
初學階段時,恩華遇上一位很有耐性的二胡老師,願意親自手抄大字版曲譜,譜上一個音符足有半個拳頭大,方便嚴重弱視的他練習,「別人的曲譜可能幾頁紙就完了,但我的曲譜全是厚厚的一疊,一頁紙大概只有一兩行字。」閱讀大字譜只是學好新曲的第一步,恩華為免錯漏必須背曲,但他不曾為此氣餒,反因早期學習進度快,初學第三個月已於內地的小比賽獲獎,以至他愈拉愈起勁,極速跳級考試,短短兩年已考得中央音樂學院十級二胡資格。
兩年考獲十級二胡資格
儘管恩華取得高階評級、囊括多個獎項,但速成之下的基本功並不紮實,他的拉琴手勢也太繃緊,遭受「操之過急」的批評。他深知若不改變,其琴技勢難進深,惟有痛定思痛放棄舊有,從初級技法重新練起,「當時日練八小時,拉長音、音階,學習控制身體,放鬆手部肌肉。」在那新舊磨合的痛苦階段,恩華拉出的音色連自己也受不住,令他一度想過放棄二胡,整天懷疑自己是否適合演奏,直至他慢慢苦練出正確基本功,才重拾對二胡的初心。
十年習琴,昔日恩華喜歡拉奏節拍明快的《賽馬》、《戰馬奔騰》,但隨着年紀漸長,如今他偏愛有故事的歌,表演《梁祝》便把自己當作梁山伯,又化身為《江河水》哭崩長城的孟姜女,盼代入各曲中人物,把故事說得更精采,「習琴第三年我首次拉《二泉映月》,但那時只拉出音符,奏不出滄桑感,經歷增加使我有更多體會,這首曲值得演奏一輩子。」
視力再減看譜變背譜
恩華克服了學二胡的困難,亦曾捱過最難突破的瓶頸,然而,上天給他的噩耗不絕,去年某天他一覺醒來,赫然發現視力再次下跌,連大字譜也看不清了,眼前有人都只見形狀,假若對方不說話,他根本不知前方有人。驚慌過後,恩華逼自己盡快平靜下來,「以前我改變技法的階段都沒放棄,此刻更無理由放棄,想辦法解決就好了。」
沒有眼看,還有耳可聽,恩華現時每堂一小時的課,有一半時間皆由老師讀譜,「我必須知道音符是幾分,八分的、四分的,不能單靠聽錄音,這樣並不專業。」課後他回家聽錄音,繼續努力背譜,學習效率固然比健視樂手慢一半,一年頂多只可記下兩首曲,背錯還得重新再來,但他對自我的要求並沒因此下降,花上半年時間熟記歷時二十九分鐘的《梁祝》,旁人聽得驚訝,他卻看得淡然,「拉完好過癮,其實二胡是單聲道,背起來算是容易,反觀鋼琴奏鳴曲更長,同時一拍有多音。」
內心比眼看得更廣闊
二胡成為恩華不可割捨的夥伴,「它不論何時都陪伴我,在我讀書成績變差時,拉琴讓我重拾快樂;遇上特別高興的事,我也想拉琴跟它分享……它也為我帶來許多朋友。」四年前他移民到香港,二胡讓人生路不熟的他,偶然在街頭結識了多位「忘年之交」,有深水埗街上賣手造二胡的人,又有在公園拉二胡的伯伯,他們為恩華找到繼續讀書的機會,更曾資助及陪伴他到上海參賽;學校又建議他參加一五年的《藝無疆:新晉展能藝術家大匯演》,他拿下個人特別獎後,獲香港展能藝術會提供資源栽培,「我很感激他們對我的奉獻,這亦成為我一直走下去的動力。」
「視障令我無法看見指揮,難以參與樂團,雖有遺憾,但我仍相信塞翁失馬,焉知非福。」恩華笑說,內心比眼所能見的更廣闊,想像力把他帶到不同意境,除了專注演奏,再無其他事物可教他分心。他拿起手杖,雖然走得比人慢,但是持着琴弓,演奏成為最公平的舞台,只要努力,看不見的曲譜仍可於手中奏起。 (系列完)
記者 李卓穎 攝影 郭顯熙
全文刊於《星島日報》